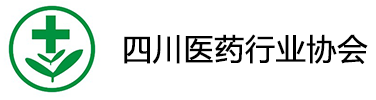西藥制劑全球競爭如同賽跑,中國“參賽”企業有了起色,整體競爭力還不盡如人意。對于一些資金充足的藥企,出海投資、并購不失為一條國際化捷徑。
(絕大多數中國藥企進入國際市場的主要方式還是以貿易為主。如果將西藥制劑參與全球市場競爭比作一場賽跑,歐美藥企、甚至印度藥企,早已跑出一大截,中國藥企算剛起步。圖/視覺中國)
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副會長孟冬平,仍記得5年前的尷尬場景。2012年,孟冬平帶隊國內藥企到俄羅斯訪問,一名俄羅斯客商對她抱怨,希望能從中國進口更多、更高質量的藥品。
當年,全球藥品市場上的中國本土制劑屈指可數。2012年中國藥企在美國仿制藥申請(ANDA)獲批總量僅為11個。如今,孟冬平再次帶隊出訪時,不再擔心尷尬重現。
至今已經有80多個中國制劑企業的近百個制劑,在歐美市場上實現銷售,已經注冊和正在注冊的產品超過200個。
隨著鼓勵制劑出口政策暖風頻頻吹來,中國本土制劑出口的呼聲愈發高漲,但在國際市場競爭中,中國本土制劑企業卻腹背受敵:高端產品上競爭不過歐美企業,低端產品上競爭不過印度企業,更重要的是自身實力不過硬。
中國本土制劑最終能否拓寬全球市場的征程,走出低速增長的泥潭,在藥品生產、創新研發、并購等“招式”中增強取勝,還需要經過更多的考驗。
“走上去”,才能賺到錢
在國際分工協作中,中國藥企長期處于價值鏈底端,消耗國內能源,利潤大頭在外國藥企。在醫藥價值鏈四個環節,中國藥企僅在生產制造環節具有一定優勢。“這并不是真正的國際化,只是貿易的輸出。”孟冬平指出。
由于行業門檻低,一大批企業爭相涌入,從2009年到2016年,七年間經營醫藥產品出口的企業數量增長63%。結果是原料藥產能嚴重過剩,出口議價能力減弱,國內企業內仗外打,客戶左右殺價。
“有點像過去的稀土行業,自己企業和自己企業競爭,把市場攪得一塌糊涂,都無利可圖。”中國醫藥管理協會副會長王學恭說道。據了解,中國化學原料藥出口平均利潤僅5%左右,而化學制劑的凈利潤率普遍在30%以上。
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數據顯示,相比5年前的6%左右,如今西藥制劑出口量在藥品出口中的比重提升到10%以上,但原料藥的出口比重仍超過八成。如石藥集團每年6億多美元的藥品出口額,九成以上由原料藥貢獻。
嘗試出口高附加值的制劑,成為藥企突圍的一個選項。多數企業首選發展中國家作為第一站。之后,一些藥企開始承接國際合同加工業,即利用國外藥企的批件做國際代工。
承接代工生產的藥企,必須符合歐美cGMP要求,這意味著耗時長、耗資大。《財經》記者了解到,某條制劑車間為了通過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認證,5年間花費近2億元。轉移到中國來的大多是一些老仿制藥品種,利潤不高,市場波動大,常面臨價格競爭失利而退市的風險。
出口試劑,中國藥企的主要機會在于專利過期階段和之后的通用名階段,包括專利過期后仿制、挑戰專利、專利期內授權仿制。對絕大部分中國企業而言,目前還不具備挑戰專利和獲授權仿制藥的實力,在專利過期之后進行通用名藥領域申請或購買ANDA生產許可,進入歐美主流市場是目前的現實選擇。
2016年12月,在齊魯制藥首批粉針制劑出口美國發運儀式上,齊魯制藥副總經理鮑海忠多次摘下眼鏡擦眼淚,“太不容易了。”這是國內醫藥企業首次實現頭孢類注射粉針劑出口美國。
一個出口制劑從初始研發到最終上市一般要經歷四五年時間,投入百萬至幾千萬元。其中需要經歷研發、確認批和注冊批的生產、穩定性研究和注冊資料的編寫和申報,獲批后還需要進行包括序列化在內的包裝設計、生產組織、產品放行以及物流選擇等一系列上市準備的工作。據齊魯制藥國際認證工作負責人回憶,該企業的制劑剛出口時,最大的難點在于:國外尤其是法規市場對中國制藥企業的認知度和“中國制造”品牌的認可度低,“需要不斷申請并獲得國際認證,逐漸獲得認可,制劑出口一步步做大。這的確需要一個過程”。
而“美國制劑市場對質量特別關注,一旦出一次質量問題,對企業以后市場的影響就會非常大。”一醫藥公司進出口業務負責人對《財經》記者說。
2009年到2017年,美國FDA對40多家中國藥企發出過進口警示,其中不乏大型藥企。尤其是近幾年,FDA對中國原料藥和制劑的監控,由抽查變為常規檢查。主要問題是在數據,包括數據不完整、數據不準確、分析報告造假、記錄更換內容、重抄記錄、日期與簽名不一致等。
如何走出國際范
絕大多數中國藥企進入國際市場的主要方式還是以貿易為主。如果將西藥制劑參與全球市場競爭比作一場賽跑,歐美藥企、甚至印度藥企,早已跑出一大截,中國藥企算剛起步。
美國FDA官網數據顯示,2016年FDA批準了22個來自中國藥企的ANDA申請。
2017年上半年,又有18個ANDA文號獲批。這與仿制藥冠軍印度藥企相比,尚顯羸弱。
據粗略估計,幾家真正走出去的國內藥企,每年的制劑銷售總額為2億多美元,相比之下,印度排名第三的藥企在美國市場的年銷售額就有十幾億美元。
一個藥品專利到期后有一個短暫盈利窗口,印度企業、歐美本土的仿制藥企業已經把這個填滿了。“對一些已經專利到期很久的產品,我們其實已經沒有什么機會了。”王學恭告訴《財經》記者,“很多中國企業在美國只注冊兩三個品種,很難形成國際化規模銷售。”
制劑規模化出口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國外仿制藥發展不同于中國,一個產品的生命周期可能會很短,企業一個仿制藥上市三五年后一般會推出新品,不斷填補空白,這是一個持續動態的過程。藥企的國際化戰略,離不開一系列產品布局、持續的研發注冊、對歐美市場的對接和開拓能力、符合標準的生產場地等諸多條件。
王學恭分析,所幸每年總會有一些專利到期藥物,如果這些品種抓得好,抓住窗口期去做,可能有機會突圍;國內藥企有原料藥優勢,對于一些量特別大、成本構成比重高的產品,可以利用原料制劑一體化的綜合優勢。
像當年印度制藥企業一樣,發展較快的幾家國內龍頭仿制藥出口企業開始通過并購加速國際化,這是近些年國內藥企走出去的有效路徑之一。
復星醫藥副總裁汪曜、人福醫藥國際投資與業務發展董事總經理Jason Zhang皆表示,通過并購和投資,企業不僅獲得了海外的技術,還可獲得全球的銷售網絡,利于自己研發的產品與并購的產品,直接進入全球網絡,實現在海外布局業務的同時,還可以幫助升級國內的經營。
2016年,大中型醫藥企業的海外并購案例達到25個,并購總金額達55億美元。如綠葉制藥以2.45億歐元收購瑞士公司Acino旗下的透皮釋藥系統業務,獲得了產品線、位于德國的生產制造中心、商業體系,并獲得全球范圍內20多個優質合作伙伴;同年,人福醫藥收購美國Epic Pharma,未來有望擁有超過100個ANDA批文;2017年復星醫藥以10.91億美元收購印度藥企Gland pharma74%的股權,刷新了中國藥企海外并購金額紀錄。
投資、并購并非“買買買”那么簡單。以綠葉制藥收購瑞士Acino公司透皮釋藥物業務為例,此次收購屬于招標項目,綠葉在前期做足了盡職調查,充分評估其潛在的商業風險,并挖掘其商業價值,重點評估標的公司能如何給自己的未來作出貢獻、要帶產品與技術到中國來,以及能否產生更多的業務和協同效應。
“并購后的整合很重要,很多公司合并、收購完成了,發現很難整合。在商業談判階段,需要有足夠的團隊進行對接。”綠葉集團副總裁姜華事后總結經驗時分析。
如果企業沒有成形的國際化戰略,盲目并購會有風險。“看一個國外企業,光看它的財務報表不行,還要衡量企業是否真正了解國外市場的商業模式、運作規律。”王學恭說。
近些年,國內外大型藥企還嘗試一條新路與中小創新藥公司合作。美國輝瑞制藥有限公司大中華區總裁吳曉濱曾表示,跨國藥企可以與中小創新藥公司,開展多種形式的藥品研發合作,“鼓勵創新藥公司的投資、建設,賦予小企業自由”。
從仿制、仿創結合,到創新藥,中國企業雄心勃勃。目前國內有十幾種創新藥獲美國FDA批準進入臨床研究階段。不過,對于中國藥企而言,現在處于陣痛期。一些藥企在創新藥與收購方面還沒見到回報,但為了產業升級與戰略調整,不得不下狠心停掉仿制藥和原料藥的訂單。
對標國際,政策催動
標準不一,是過去中國制劑出口面臨的最大困境。如今,多項鼓勵制劑國際化的政策已連續發布,這種情況或將改善。
中國的標準制定多考慮各區域市場生產技術水平、藥品檢驗水平和經濟發展能力,相對國外,國內產品質量標準在制定過程中相應偏低。綠葉制藥董事長劉殿波曾尖銳指出,中國過去20年是個特殊的時期,業內人都有種投機心理。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真正出力,按照國際標準做事。
國內的GMP也是參照美國的cGMP制定的,但在執行層面,大多數藥企認為GMP太麻煩,并不嚴格按照GMP來管理,監管部門查得也不嚴。石藥集團中央藥物研究院三院副院長李銀貴回憶道,四年前,企業開始做美國制劑出口、申請美國市場的“通行證”時,美國FDA嚴格按照cGMP的標準進行現場檢查,不少制劑申請倒在這一關。
彼時,國家食藥監總局(CFDA)的監管體系,特別是產品審批、標準管理、檢驗檢測與認證等方面尚未與國際接軌,導致GMP標準無法被其他國家認可。一家藥企欲擴展國際市場,不得不重做臨床試驗,全部的審批文件也要重做。2016年,CFDA發布關于優先審評審批范圍的政策,明確在中國境內用同一生產線生產并在美國、歐盟藥品審批機構同步申請上市且通過了其現場檢查的藥品注冊申請,可優先審評。
中國市場本身也需要這樣的提升。如劉殿波所言,如果還把中國市場看成一個本土市場,就Out了。據IMS報告顯示,2014年,全球藥品市場9761億美元,其中,中國藥品市場占總額的11%,而美國市場占39%。
2017年6月,中國成為國際人用藥品注冊技術協調會(ICH)正式成員。企業將可以按相同的技術要求向多個國家或地區的監管機構申報,不用再做兩個一模一樣的臨床試驗。
“中國早就加入WTO,各國在醫藥貿易上多少都會有一些保護主義,但也只能提升準入標準來設置障礙。只要我們的標準實現了與其在臨床試驗、生產制造等方面的標準一致,會受到公平待遇。”姜華說。
10月8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關于深化審評審批制度改革鼓勵藥品醫療器械創新的意見》,提出36項改革措施,明確指出歐美獲得認證品種將具有優先審評資格;此外,還規定達到國際標準的仿制藥注冊時可以豁免一部分臨床試驗、招標時有單獨的質量分類標準、知識產權的保護等。
然而,對于走在國際化路上的藥企,這股政策暖風需要更加細膩、有力。“國家層面對于整個行業發布了很多政策,指導原則與框架都是利好的,但現在還需要具體的實施細則。要不然,企業不知道怎么去做,監管部門也會不知道如何去監管。”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財經》記者。
醫藥行業是受政策與監管影響較大的行業。“制度改革可以釋放生產力。”博瑞生物高級副總裁王征野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分析,真正有實力的企業對有利的政策高度敏感,只要政策稍加支撐,企業就能乘勢而上。
中國制劑出口的春天,到來尚需時日,但至少風已經吹起來了。(來源:醫藥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