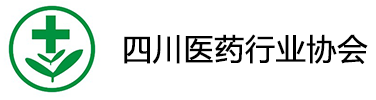有業內人士預測,隨著以醫藥分開為核心的公立醫院改革持續深入,醫院處方終于有了流出的跡象,處方藥零售已走出堅實的第一步,在多種舉措的加成作用下,以點破面只是時間問題,“到2020年自院內向院外遷移的處方藥總量有望近萬億。”
如此龐大的市場機遇,是否就等同于零售藥店的大擴張時代?答案似乎還不確定。
更強對手:
基層醫療機構
隨著全國公立醫院全面取消藥品加成,推進醫藥分開,處方藥外流將給基層醫療機構以及零售藥店帶來發展機遇。
目前一心堂、大參林、老百姓、益豐藥房等四家A股上市藥店均有所布局,嘗試借助承接處方提升銷售規模。其中,網絡醫院落地就是一大關注要點。但分析人士也強調,為滿足處方藥銷售嚴謹的要求,零售企業技術人員專業化很重要,只有解決處方權問題才能真正促進處方藥銷售,是促進零售規模持續提升的重點。
對零售藥店而言,在現有的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下,并不能理所當然地成為處方外流的唯一或第一選擇。盡管其中一個競爭對手醫藥電商,自今年“兩辦”36條后,處方藥板塊喊停,未來或與實體零售將走向統一。但更強力競爭“對手”——基層醫療機構,以先天擁有被納入醫保體系,且坐擁多重政策優惠、高比例報銷等條件,占據優勢。
老百姓大藥房連鎖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劉星武坦言,醫院藥品加成取消后,基層診療機構的慢病用藥目錄擴大,零售藥店經營也許會更艱難,尤其是中小連鎖藥店受到沖擊較大。處方藥外流對零售市場的影響還有待觀察。
最大紅利:
有能力者得
記者注意到,近兩年省市藥房都在試點開診電子處方,竭力分得處方外流的一塊蛋糕。廣西梧州處方共享平臺參與者梧州百姓藥房董事長孔建光就表示,處方外流的紅利最終將落入少數藥店囊中,從醫院溢出的處方并不會平均分配成44萬份而輸入每家藥店,而是在行政干預和市場競爭中集中在一定范圍內。
孔建光認為,決定外流處方吸收量的關鍵因素,一是企業的供應鏈整合能力,即儲備品種是否能夠與醫院形成互動與互補,二是企業的專業服務能力,能否保證患者的用藥安全性和依從性。
有接近商務部的行業專家表示,2018年零售藥店行業或將有大洗牌。早前商務部市場秩序司和國家食藥監管總局藥化監管司就《關于推進零售藥店分類分級管理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向湖南、湖北、河北等省份的商務主管部門征求意見,按照文件內容,除將藥店分為三個類別外,還將對同類別的藥店進行細分。根據服務能力(藥品供應能力與可追溯管理水平、藥學服務項目、藥師配備情況、信息化程度),將零售藥店在同一類別內由低到高劃分為A、AA、AAA三個等級。
其中三類藥店的一類藥店不能再賣處方藥,二類藥店可經營非處方藥、處方藥(限制類藥品除外)和中藥飲片;三類藥店可經營非處方藥、處方藥和中藥飲片。實際上,藥店分類分級管理幾年前已提出,一類零售藥店經營范圍限定為非處方藥,也就是包括甲類和乙類OTC藥品,比上述《征求意見稿》中的一類藥店多了甲類OTC可經營。
從政策實踐來看,各地已經不同程度地開展藥店分級管理試點。以上海為例,發布的《零售藥店評級現場評審評分標準》共設4個大類、21個項目、81個條目,覆蓋現場硬件、基礎管理、藥品供應、票據管理、人員配備、知識培訓、藥學服務等各運營管理環節。
從行業到企業,處方外流會被進行二次分流,如何使自身成為最終受益者,需要從業者依自身內外部環境、上下游資源合理構建模式。
最可行方案:
制造與零售合力
醫改帶來的政策紅利,具有無限的想象空間。不過,要實現處方藥在院外銷售,信息化建設尤須加快。藥企、醫院、藥店、患者以及醫保等行政部門間的信息如何實現聯通,這是實現以處方共享平臺為中心的外方外流推進過程中亟需解決的問題。此外,電子處方的合法化的問題仍待解決。目前各地針對電子處方進行了“不定向”的試點,如何制定自上而下的統一管理辦法,成為影響進度的關鍵。與電子處方、電子病歷高度關聯的電子簽名也仍待相關法案的出臺。
業內專家建議,零售藥店要從處方外流中獲益,須進行相應的改造升級。一是參照有關條規政策要求,加強藥店整改晉級,獲取處方藥品銷售資質;二是增加招聘執業藥師數量及比例,加強店員的執業培訓,提高藥店整體專業水平。甚至,還可考慮重新選址搬遷或建立新藥店,在縣級醫院出口或緊鄰位置,爭取“截留”地理優勢。
要把握處方藥外流機遇,做大蛋糕,零售行業人士認為,制造+零售形成合力是一條可行之路。云南鴻翔一心堂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總裁趙飚就表示,處方藥從生產企業直接到零售市場,必須有一個相對安全穩定的渠道。生產企業應該跟連鎖藥店共同探索合作方式,迎接零售市場的大變革,贏得市場先機。劉星武也指出,零售藥店可以聯合生產企業共同挖掘客戶的個性化需求,通過更專業的指導和服務,促進處方藥在零售終端的專業銷售和穩定增長。(來源:醫藥網)